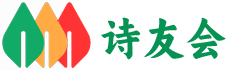|
第一章、羽翼般的旋律
每次写一首诗歌或是一篇文章,我都会刻意地寻找到一段旋律,它也许是一首有词的歌曲,也许是一首轻音乐。我总要凭着当时的心境寻找到一段最能衬托那份心情的旋律。若是找不到,所有跃跃欲试的灵感就会被困在没有出口的黑暗之中,狂躁到快要爆炸。但是在很多时候,我总是能幸运地找到那一首与之最有机缘的旋律,听之,思之,任清泉似的灵感在心头与思绪里不断地涌现。那颗躁动而又孤傲的心瞬间被驯服了,那旋律有着神的魔力,只要轻轻地响起,就能让灵感化作一对会飞的羽翼。
而今我又找到了一段合适的故事旋律,带我飞,带我去寻找那飘忽的记忆。我要掸去这厚厚的灰尘与一些清晰的或是烦乱的往事,我可能早已把那些故事遗忘,而今它又因为我偶尔翻读的一页文字,一个似曾相识的故事,悬挂在我心底的门窗。
第二章、最初的记忆
25年前的那个深秋,下着冰条似的雨。我从妈妈的身体里惊慌而又新奇地坠落这个世界,墙头上并没有凤鸟的歌唱,妈妈的梦中也没有开出奇异的花来。也许我就只能是怀揣着一个巨大而又美丽的梦,独行在这一世无语而玄之又玄的人生。
从一岁到三岁我几乎是没有能留下任何的记忆,抑或是那些记忆被偷走了。无论我怎样的苦思冥想,就连梦中也找不到半点残存的影子。我在想,如果人一生那些痛苦的记忆,能够交付给孩童时代该多好。
当然从一岁到三岁的故事还是可以从大人们的记忆中找出一些的。他们总是说着模棱两可的答案,一会儿说你出生在早晨的7点20分,一会儿又说你是出生在晚上的9点。但唯有大姑姑的那一段关于我的记忆是最可信的,其实并算不上是什么故事,只不过是让我想起来就会甜美地笑罢了。我大姑不只一次的在我面前感叹地讲起我刚出生时候的样子,雪白的皮肤,脸上两片灵动的粉云。到现在她还是忍不住怀疑,那两片美丽的粉云一定是妈妈偷偷地给我擦上了胭脂。
我想,那时候我一定是格外的美丽,不然大姑姑干嘛总是怀疑地感叹呢?到现在,我仍是对那时的自己羡慕不已,就好像是在羡慕着别人的美丽。而如今我这疲倦麻木的眼神,惨白又毫无血色的面容,似乎实在是与那个美丽的婴儿扯不上半点的关系。
四岁之后就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记忆,但每次我讲的时候,长辈们总是不相信,他们怀疑地说:“你准是又听奶奶告诉你的吧?”谁能相信四岁时我们家的大门是朝西的,土墙的表面全是黄泥和碎碎的麦秆泥成的。天知道后来怎么会朝南了。
第三章、心头那第一道伤痕
小孩子们总是贪吃的,大概是我五岁的一个秋天的晌午,我们村子里那个老头又在围着满村子吆喝着:“鸡骨头,羊骨头咱都要……”他满三轮车里都拉着五颜六色的玩具和糖豆,应该还有仙丹(是像传说中的仙丹的模样又酸又甜的褐色糖豆),气球,花头绳,粘牙糖和各种玩具,还有一些大人们需要的针和彩线。总之他那一车的新鲜玩意儿,就像一个永远探索不尽的五彩斑斓的梦。有时我怀疑自己记错了,难道二十多年前就有三轮车了吗?但我还是肯定那个时候他就是推着个三轮车的。还有我总是想不通他究竟要鸡骨头羊骨头干嘛去呢?总之那天我是拿了一双,我自己认为肯定是再也穿不着的鞋子,兴高采烈的跑去换了一包五彩的糖豆回来吃。结果被奶奶发现了,她并没有责怪我,只是恨恨地告诉我,那些糖豆全是毒药,吃了就会死。我听了之后就惊恐地坐在堂屋的门栏上,一边大哭着,一边用洗衣粉水不停地刷着吃过糖豆的嘴巴。我多想,让现在这个长大成人的自己穿越到那个时光里去,去抚慰那一个小可怜儿的自己 ,告诉她那糖豆里没有毒,更不会死。我还要送给她一大堆的糖豆,送给她一个五彩斑斓的最甜最甜的童年。虽然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死亡究竟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但还是莫名地害怕着死亡,就像惧怕着一个不可知的黑洞或深渊,那一定是一个去了之后就再也见不到妈妈的世界,那一定是一个再也没有糖豆的世界。
我深记得那天村子里的几个来与奶奶闲谈的妇女都嬉笑地望着我用洗衣粉洗嘴巴的样子,为什么她们都不能够懂得我那一刻有多么的恐慌与无助呢?他们那样冷漠的嬉笑,在我小小的心上狠狠地划出了人生的第一刀伤疤。那笑一直阴森地回荡在悬崖峭壁上,不停地嬉笑着,再狂笑着,再冷笑着,直到望着我落入万丈深渊。那会儿妈妈去哪里了?如果她那一刻见到我会心疼吗?每当回忆起堂屋门栏上那个一边惊恐地大哭着,一边无助地用洗衣粉水洗嘴巴的小女孩,我觉得是一个多么可笑可爱的故事。
第四章、粪窑子让我想起的那些事
虽然我真的不记得我们家的大门是在什么时候改成门朝南的,但我却记得门朝南的大门前有一个很大的粪窑子。那时候好像每家门前都有一个那样的或大或小的粪窑子,大概是用来积攒粪便和垃圾的。经过长久的积累和发酵,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拉到地里当化肥。关于粪窑子也听长辈们讲起很多故事,记得最深的就是就大姑和奶奶讲起的邻居家的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女孩掉进里面溺死了。那经过长久发酵的粪窑子就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沼泽地,好像当时大人立刻就把小女孩救上来了,但那可怕的粪便与驱虫已经糊满了她的嘴巴,眼睛和耳朵。可怜的小女孩最终还是死掉了,她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呀,这也许是她父母一生的痛吧。为什么那个时候每家都要在自家门前弄那样一个可怕的粪窑子呢?大概是从那以后我们村子里每家每户的粪窑子都被瞬间填平了,同时也叫醒了那些愚蠢的人们头脑里的隐患意识。
讲到这件故事我也想起了长辈们经常提起我小时候的一件危险的事情。那个时候大概我也是一岁左右吧,大人们那段比较忙,除了吃饭睡觉基本上都是在地里干农活的。我和堂哥年龄相当,奶奶和妈妈就把我们这两个刚刚学会爬的小娃娃留给了70多岁的老太儿(我们这都管爷爷的爸爸叫老太儿)。70多岁的老人带孩子实在是靠不住的,他经力不够还总爱打瞌睡,结果那天老太儿就睡着了,我们家猪圈里有一只常年圈着的非常凶猛的大猪,它简直就像一只饥饿的疯狗,每次我们家的鸡不小心闯进去它都恨不得撕碎之后全部吞进肚子里去。老太儿睡着的那天,我就像一个迷途的小怪物也一步一爬地误闯入了猪圈里,当我离那凶猛的怪猪还有一米远的时候母亲回来了。她赶紧后怕地将我抱出了那个充满死亡气息的猪圈。这多像惊险电影里的画面呀!后来父亲和母亲还总是后怕地提起这件事情,如果当时爬我果真爬到那头凶猛的怪猪身边它真的会把我吃掉吗?
提起这事怎么突然又想起了去世十八年的老太儿呢?他现在在哪里呢?也许成了今生与我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也许成了纯真无邪的小少年。呵,我自己都忍不住轻笑自己这些不着边际的想法了。感谢老太儿送给我的第一个名字“金穗”,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就像是一个骄傲的小公主。虽然爸爸妈妈最终也没有选择这个名字做我的大名,虽然所有的人都不再称呼我这个名字。但我还是会一再感动地、失落地、无奈地想起老太儿送给我的这人生第一个名字。
又想起了老太儿每次赶集回来都会给我们姊妹四个带回好吃的,虽然他总是重男轻女,把又大又红的苹果给堂哥和弟弟吃,把廉价的蕉酥果儿给我吃。但我还是想念他。
第五章、最初的友谊
我们西边的邻居家来了一个帅气而又机灵的小男孩,一飞。说是邻居吧,好像有点远了,其实那家的男主人与我老太儿是亲兄弟。因为他的儿媳妇生不出男孩,可能是经过了一家人的慎重商量之后,那儿媳妇就从自己姊妹家要来了男孩一飞。他与我同龄,我是九月生,他好像是正月。说不出是怎样的一种默契,从此我们就成了唯一的好朋友。已不记得我们究竟做了什么好玩的游戏,总之我们就是好朋友,除了吃饭睡觉,我们总是黏在一起。
大概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我一起床没来得及吃早饭就慌忙跑去找一飞玩。我欢快而急促地敲响着他们家那矮小而没有上漆的木门,很久大门才迟钝地被打开,我看见一飞的爸爸还躺在门楼子里的驾车子上蒙头睡觉。一飞奶奶在来给我开门的时候,又顺便要叫醒一飞爸爸起来吃早饭。一飞看见我来,也小鸟儿似地朝我跑来。一飞奶奶一直连着叫了几声,一飞爸爸都没有回应,任凭怎么叫也没有半点回应,一飞奶奶只好掀开蒙着一飞爸爸头的被子。原来他是死了,我真想不起当时一飞奶奶看见自己儿子死了是什么样子的反应了,他们一家是嚎啕大哭了吗?还是悲伤到静止不动了。我甚至不记得一飞爸爸的面容是什么样子的了,但他驾车子上耷拉下来的那一只死黄而又僵硬的大手,却成了我对死亡最初的记忆。
人们总是在议论着,在不懂着。为什么一飞的爸爸在门楼子里睡了一夜,看了一夜刚出生的猪娃子就无声无息地死了呢?有悲伤的,有惋惜的,有麻木的。一飞爸爸的后世办完之后,一飞的妈妈就把他送到他原本的亲爸爸亲妈妈身边去了。从此以后,我就失去了这一个人生最初的朋友。后来我听说一飞的妈妈改嫁了,没几年她新嫁的那个男人也去世了,有一些人议论着说她一定是克夫。而关于一飞的消息我再也没有听说过了,他的名字总是像童年里一个模糊却又有点悲情色彩的梦,我时常又做起这个梦,却总还是看不清他的样子。这一生我们还会再见面吗?也许我们将这样永远地远离彼此了,也许多少年后我们真的会再见面,但谁又能认得最初的对方呢?
第六章、美丽的葡萄架子我的梦
也许是孩子,也许孩子的记忆总是很容易就忘记。渐渐的关于一飞留给我那些记忆我也就真的淡忘了。后来我们一个大家庭就组织了分家活动,我和弟弟就跟着父亲母亲搬到了南面的新宅子里。那是一个还算大的院子,大门是朝南的,大门的颜色仍旧是没有上漆的木头色,贴着喜庆而又让人很有安全感的门神。其实我更喜欢没有上漆的木门,原始而又亲切,上了红漆的木门总是让我莫名地与上了黑漆的棺材联想到一起。门楼子前面是爸爸搭起的一个很有浪漫色彩的葡萄架子。夏天里葡萄叶子长美了,爸爸就会在葡萄架子下面放一张小竹床,躺在小竹床上冰凉冰凉的。闲暇时,我和弟弟总是会悠闲地躺在竹床上,脑袋枕着小手臂,仰望着葡萄叶子缝隙间那美丽而又斑驳的影子,幻想着不着边际的梦想。每个夏日的夜晚我们总是依偎着,躺在竹床上的爸爸的怀里,听着不知名的虫子时断时续地唱歌,听着爸爸神秘而又动听的故事安心地睡着。二十年以后,那一个美丽而又浪漫的葡萄架子,仍旧是我没有能够实现的梦想。我也想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葡萄架子,一张水泥做的圆桌子,一张摇摇椅,一杯红酒,一本书,一首轻音乐。
我们的新房子是青色的砖块盖成的,也许当时家里实在是经济困难,所以我们的房子既没有别人家的高大,也没有别人家的宽敞,连厨房才总共三间。小小的昏暗的卧室和客厅连在一起,而厨房在卧室的南面另起了一个门。院子里有七棵很大的柿子树,听爸爸说那些柿子树比我和弟弟的年纪都大呢,到现在都快30年了。每到柿子成熟时,我和弟弟总是村子里别人最羡慕的孩子,因为我们有吃也吃不完的甜柿子。爸爸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很深的地窖,他把那些快要熟透的和还没有熟透的柿子分类放在地窖里储藏。奶奶和爷爷就会拉着满驾车子熟透的柿子到集市上去卖,当然每次都要拉着我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弟弟。
我们家门前还有一大片的杨树林子,那时候我们村子里总是有几片很美丽的杨树林子,在每个孩子们的心中那就最神秘的大森林。每到夏秋的傍晚,我们一群小孩子拿着手灯可以在林子里摸到许多肥美的蝉,拿回去叫大人们给我做成美味。最难忘的就是大娘在那小小灶屋里炒蝉的样子,每一次她都是熟练地在锅里淋上油,用微火反复的煎,反复的焙,焙干那多余的水分,蝉肉的香味和着油香就瞬间在灶屋里诱惑地弥漫开来,飘出了窗子,飘出了门口,飘出了院子…我们姊妹四个就忍着口水,眼巴巴地望着,期待着。那种肉的肥美和香味是任何美食都比不上的。此生都无法忘怀,但是再也没有机会品尝到了吧,即使有机会,也不会有勇气去品尝那样奇怪的虫子了。
杨树林子东面两三米处就是一处坟场,大概有十几座坟。那个时候并不害怕坟,我和小朋友还时常爬到坟上玩耍。因为我们村子里条件不好,夏天又没有风扇,屋子里特别闷热。每到傍晚几家邻居就会早早地在挨着坟场不远处,成排地铺上自家的席子,在那里端着自家的饭菜,围坐在一起。一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一边不顾形象地大口吃着。
伴着傍晚凉爽的风,和着各家的饭菜香,夜幕也渐渐地来了。大家就非常放松的躺在自家的席子上,有的望着天上的星星,有的闭目养神,有的又你一言我一语的聊起来天来。有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会缠着邻居家的爷爷奶奶或大叔大婶们讲几个有趣的民间鬼故事,很多时候故事没有听完就窝在母亲的臂弯里睡着了。
|